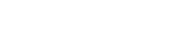我的发梢带来一片海,沉没西安的风里。在祖国中央的长安,我想着青岛的那片海。
几日前母亲寄来一箱鱼片,打开后扑面而来一股潮汐味儿,把我卷进故都的回忆。
以前坐公车转悠,穿过海平面以下82.81米的隧道,沿环岛西路,走到陆地最终端的海岬,就到了鱼鸣嘴,一个小渔村。
传说每到渔汛的时候,在深蓝色的海底,黄花鱼和黄姑鱼在水下窃窃私语,信息的泡泡浮上海面,让渔人听上好一阵。村里的渔人说,以前打渔的时候,鱼鸣绵延数百里,他总要边听边笑,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下网。深处的鱼上到浅水,就会浑身无力。渔人用皲裂的手往箱子里放坚冰,不然,鱼易腐坏,不能送到远方。“现在的鱼,没有从前味道好了,个头也不大了,捕不着啦。”
故乡称呼渔人为“鱼佬”。他们常年吹在青岛的风里,看不出年纪。他们用干枯的手抚摸皱纹,阳光暴烈,海风硬冷,渗透进他们的肩胛骨,和我讲话的鱼佬让我想起舅舅,同样精瘦且黝黑。
从前是多久从前?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甚至可以是21世纪初的那几年,鱼并不少,黄花鱼和黄姑鱼在产卵时张嘴齐鸣。
我还记得与同行人坐在石头上,看鱼佬从船上下鱼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下鱼的场面,一垛又一垛的鱼,将它们金色或银色的鳞堆砌在一起,波光粼粼,比海面还晃眼。鱼佬的甲板随着海浪浮沉,他吼自己的伙计手脚麻利,鱼佬彪悍的口音在强硬风浪里塑造,声声逆风,多以去声,像往常他们在生死计较里挑战自然,留给海神一个勇敢的回答。“这几年打上来的越来越少了。”鱼佬点上了烟,“过两年这里就只有渔家乐,或者水产养殖了。”难以言喻的社会进化规律在鱼佬生活里发生。鱼鸣嘴用不了多久也会消失,毕竟已无鱼可渔。“海资源少了,赚不了几个,还怕搭上命,儿子住进新楼咯,不用吃这些苦。”鱼佬的烟头明暗交替,像是说给自己,也想说给海——他的良田,他祖辈的墓地。
沿着路,可以完完整整地逛一圈鱼鸣嘴。渔村总有一个标志——红旗,家家户户在屋顶上插上红旗,判断风的来去,指引航海的方向。以往遍地可见的海草房已屈指可数,屋顶用特有的海带草苫成,堆成一个厚厚的尖顶,古朴厚拙,宛如童话世界。海草房冬暖夏凉,以石为墙,海草为顶,百年不腐,是最具胶东民居特色的老房子。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,夏天的太阳晒不透,冬天的寒风也进不来,给世世代代渔人烟火慰藉。
坐在海边,身后的炊烟袅袅升起,眼前的景总让我想起王绍波的《渔歌》,男人们像耕作一样收获渔粮,身后是金黄的夕阳,落下的那抹夕阳像是渔歌的终曲,一代海的记忆也即将消失殆尽。我想着那个传说,那个在海边眺望远方,直至变成石头的女人,世间这些是否值得。海风温柔,却也锋利,在海浪的欢歌里,我在大陆和海水间伫立。王小波在《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》里说,“太阳初升时,忽然有10万支金喇叭齐鸣,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,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,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,10万支蜡烛。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,然后10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。我忽然泪下如雨,但是我心底在欢歌。”
海边的人,或许很少没去挖过蛤蜊,撬过海蛎子,捞过海蜇,海里的东西不尽,涨潮会带来新的馈赠。鱼佬说,儿子在今年冬天会把他接进城,这里的老房子也要拆迁,像他一样往生命的尽头挪动。
他老了。


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
 官方微博
官方微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