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经·七月》有言,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,深秋时节,寒气来袭,木叶飘零,北雁南归,正是古代妇人繁忙授衣的时节。授衣即制作冬衣,而捣衣是制衣之前的一道工序,所以捣衣也多于秋风乍起之时。
夜凉如水,在那幽静的庭院深处,捣衣声如同细雨般悄然响起,打破了夜晚的寂静。这声音,是古老的歌谣,是岁月的低语,也是无数女子心中无尽思念的寄托。
长安城总是那般堂皇富丽,雕梁画栋层叠繁复,飞阁流丹精雕玉砌。歌台上,凌波舞曲婉转悠扬,纤纤楚腰随风摇曳,身姿轻盈,绿云扰扰,满头珠翠精巧华美,舞动间洒下点点星光,飘来阵阵幽香。飘渺仙子惊鸿一瞥,瞳孔中承载着长安迷人的繁华画卷,熙熙攘攘的街头,人群如潮水般涌动,灯火辉煌,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街道上,群龙舞动,五彩斑斓的龙灯在夜空中盘旋,仿佛要冲破天际。酒肆里,诗人抚掌大笑,高声吟诵着新作的诗篇,手中的酒杯频频举起,一饮而尽。他们醉倒在欢歌笑语之中,仿佛这盛世永远不会落幕,灯火将永远长明。
繁华背后,不仅仅是端坐高堂的帝王的勃勃野心,更是万千城池里征夫思妇的离愁别绪。
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”巷弄里的长安不再喧嚣,月夜下是无垠的寂寥。在那河边的青石板上,或是庭院中的石臼旁,妇人手持木杵,一下又一下地捶打着衣物,也沉闷地锤击在人们的心上。木杵与衣物相触,发出有节奏的“笃笃”声,寒冷的霜露伴着杵桕声在静谧的空气中传开,传得很远,每一声都似乎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与牵挂。那捣衣的妇人,她的脸上或许带着淡淡的忧愁。她捶打的不仅仅是衣物上的尘埃,更是生活的辛劳与思念的苦涩。她思念着戍边的丈夫,那远方战场上的英雄,不知他是否有棉衣保暖,不知他是否安康。每一次木杵的起落,都像是在把思念捶进衣服里,希望这带着自己体温和关怀的衣物,能够跨越千山万水,到达爱人的身边。
玉门关外的胡笳声幽远而绵长,浸满了无尽的思念。故人戍远,守卫家国平安。他们在风沙中坚守,在严寒中屹立,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防线。明月高悬,洒下银白的光辉,照亮了每一个孤独的身影。千门万户捣衣声,伴着秋风寄向边关,那是家人无声的关怀与期盼。
何处有唉声,何处就有诗歌。“捣衣”原本只是闺中妇人的一项平凡“女红”,本不应为外人道。然而,“咚咚咚……”的捣衣声太过凄美,在月色下影彻了诗坛,回响至今。“谁家思妇秋捣帛,月苦风凄砧杵悲。”“亦知戍不还,秋至拭清砧。”“爽砧应秋律,繁杵含凄风。”……乱世之下,处处皆是砧鸣。
千古捣衣声,诉尽相思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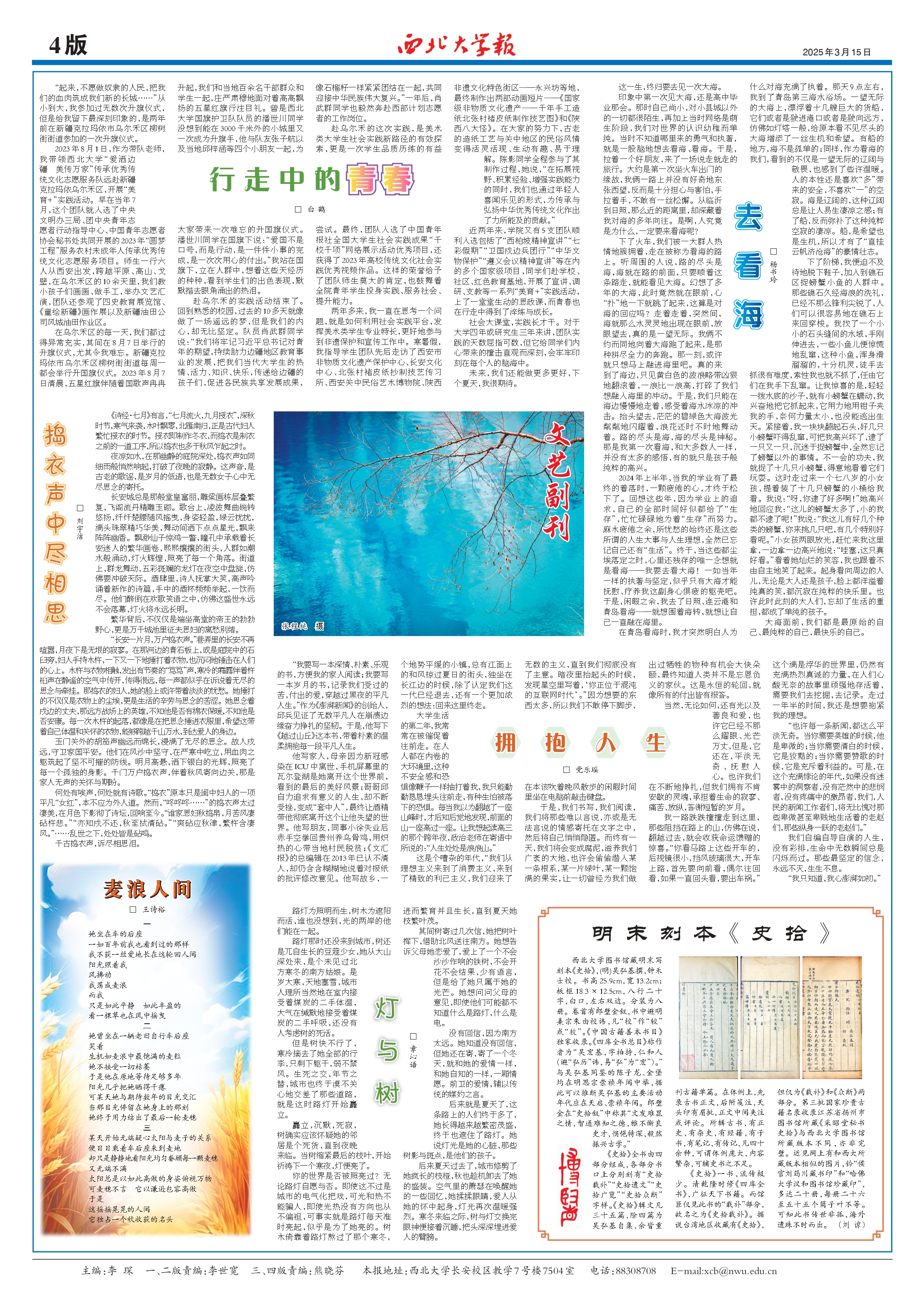
注:本文原载《西北大学报》第839期